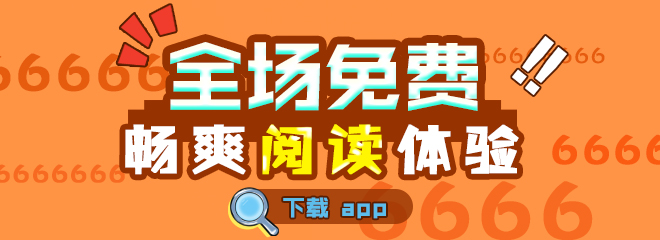其实,归纳总结起来,这古董圈子里的货源危机,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天域成立初期,低水平的生活标准,使得百姓们难有余力光顾古董这一领域。
那时候的古董文玩,民间存量虽然很多,但价格却并不高。
一至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天域的古董市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世界。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城开始大规模拆迁。
于是,在这种“打草惊蛇”之下,就出现了大量的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古董,甚至不乏惊世绝品!
而那时的这些古董的价格之低,形同于收售废品。
那时候,在那么一批先知先觉者,马上进行大量的收购,成批的贩往境外,货源流失极为巨大。
其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生活取向,日趋多元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在媒体启蒙助推之下,全民的收藏意识开始觉醒,收藏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迅猛壮大。
古董不是工业品,它的数量就是那么多,卖一件少一件,导致了市场存货日渐减少。
如果说截至上
(本章未完,请翻页)
世纪末,大家对古董收藏,尚属于文化范畴的活动,那么到了近年来,收藏古董即更多地被“异化”为投资行为。
在拍卖市场中,不乏有机构吸货者。
百姓们,也因为投资渠道缺乏和不畅,尝试把手里多余的钱投向古董市场,造成市场进一步干涸。
说白了,古董文玩,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收藏”是它其与生俱来的属性,相当一部分古董文玩,它的收藏周期非常长。
以“代”来计算。
一件被主人喜爱的古董,自收入囊中开始,不离不弃,正常的情况下,要等主人辞世之后,才有机会重现古玩市场。
有不少文明发达的国家,古董收藏传统一直延绵不断。
在市场上以“代”为周期的吐纳形式,已经呈循环之势。
而我国自1949年开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收藏才兴。
仔细算来,已经有半个世纪,至少3代人从循环“链”中脱节。
直到如今,收藏古董者,还远未到这一“代”的终结。
而只纳不吐,也是间接造成货源危机的历史原因。
那古董的货源危机
(本章未完,请翻页)
已经出现了,该如何应对呢?
应该说,国内外的古董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无法用加班生产、或紧急调配,来解决货源问题。
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根本就急不得,还需要慢慢下功夫。
首先,要培育健康的市场大环境,即良性的社会氛围。
浮躁、投机、诚信缺失、急功近利等,几乎所有当今存在的不良社会行为,无不折射于古董市场内。
因此,要好好的培养安定的社会心理。
要让人们有安全感、和谐感,提高幸福指数,提高文化品位,是艺术品市场健康发育的大前提。
同时,诸多媒体应该对古董市场,有正确的导向。
古董,自来就有艺术欣赏、和投资保值两种不同的属性。
但是,今天的媒体们,更侧重古董文玩投资的属性,催生了大量的古董投机心理。
这使得本应该宁静、儒雅、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董市场,成为了期盼发财,甚至一夜暴富的物欲场。
因此,媒体们应该更多的从艺术欣赏方面下功夫,把艺术品投资的风险讲深讲够。
这样可以使人们
(本章未完,请翻页)
更趋理性,使并不喜爱古董的投机者离开市场。
同时,应该放出手中的藏品,使古董收藏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行为。
让以收藏养收藏的人,得以收放自如,不断送出“旧爱”,收入“新欢”,促进流动,调剂市场的货源紧缺现象。
而促进古董的“回流”,也是组织货源的重要手段。
目前,因为古董市场法则的撬动,已有很多古董收藏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并购回了不少近代流失的珍品。
但是,珍品古董的国际行情,和国内基本上接轨,且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普通古董收藏者的需求。
反而,倒是中低档古董的某些品类,目前国际市场价位仍低于国内,宜于吸纳回购。
对此,应作为政策性鼓励,并以个人与机构相结合的方法,批量购进,用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
其实,如今的古董货源危机,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也会有爆发、萧条、复苏的周期运动。
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应该做好疗伤治病的细功,化淤活血,温补慢泻。
再加上天域的社会环境和谐
(本章未完,请翻页)
,人文生态优良,经过一二十年的调养,慢慢的使收藏“高热”退潮。
其实,人们早已经把古玩艺术品拍卖,划入到了市场经济概念的范畴里。
最近一两年的香城、或是澳城的秋拍,还是出了几个亿元的记录,让业界如同打了一针兴奋剂。
比如,北宋汝窑——天青釉笔洗,它的成交价为2.943亿港币。
明朝永乐年间的,铜鎏金大威德金刚,也以1.3216亿港元成交。
李可染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是以1.22亿港元成交。
而现当代的艺术王者中,旅美的华裔画家朱先生,被推上台前。
他的《工业之轮在纽约》,成交价高达1.0528亿港元。
这几次的亿元大咖们,不再是赵无极、常玉或者吴冠中了。
虽然我们希望,天域的现代艺术家们的作品,都能拍出个亿元天价,但一蹶而就,总归并非是好事。
这几次,从香城和澳城的秋拍古董专场,所拍出的亿元天价的记录上来看。
感觉要比春拍,更要实至名归一些,更比前两年的天价,更另人信服。
(本章完)